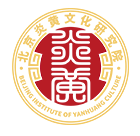于无声处写下
今夜,适合一个人静静地读书,写字
——一个人点燃一支蜡烛,沏一杯香茗
在一堆揉碎的细微中铺开,沾满浓墨
凝视亦或是回望此刻都将被允许!
一整条山谷荒废,驿道连通着驿道
头顶的盘旋上,一只青鸟高悬着悲鸣!
这是西北风串烧后的沐浴
一阵淅淅索索浅声后的,宽衣解带
月色下沐浴的冰艳美人
从她一只手摊开来的,一个青瓦明亮的屋顶
房内无人
悄一枝秃笔,在粗糙的扉页上操动了戈矛
满院月华,噙满秋水
在数度落寞后,从远处传回一两声狗吠
倒带
一当青草,重新返回草原
当羊群再化身,成苍天的白云
我就在牧歌旁,收拾那破了洞的毡房
二
遥远在辽阔中伸出手臂
揉捏一个幼年,瞬间在那马背上开花
阿妈瘦弱是那纤细的火钳
我的眼窝是铜壶,眼泪是茶
木板拼凑起的,一杯水的半悬
桌子是旧的,拼凑起来的年轮有人放下
——蝴蝶雀斑
生活
奋力在其边缘,结下厚厚尘垢后
有人失踪
一度曾被废弃的寡淡,被呱噪逼良为娼
这多像是莫奈
印象派的明暗里,空留的半悬
余下来的细碎,素衣麻履
穿过
哈贝马斯的思维边界,再次抵达神之密境
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活着
我必须承认
我必须承认这个世界的悲凉,以及
我深感的慌张和无序
我必须承认
——在我的父辈
毫无保留的教授之后,所有规则之下
才能维持的生存
我必须承认
——一个虚幻
一边搭建,一边拆除的一生
上帝啊!
它,从不会在任何具体里出现
四维,它将会是一扇洞悉之门
是的,我必须承认……
井
记忆中的老井上,始终
安放着,一个硕大的辘轳
——心空的
卷起来时,是一整个的春夏秋冬
放下来,又是一村人的黎明
黄昏,它是不该这样匆忙的
它必须是要待在,深冬里的雪落
并且一路印上,深深浅浅绵延十里的歪斜
——也就是,这一段里的空闲了
才让他们在枯燥里,稍微添加有些许耐心
——有时间
等,泉水从井底冒上来
等,心里再住下另一个人
二十四点之后
是夜四周,万籁俱寂
我已,听不见任何风声
再与你相关
点点星辉
也因此在窗棂上满溢
且
——几欲潜我深梦
在梦境里,幻化
出另一个你
周身冷焰站满廊外
过天门东之所不见
这里的春天已,不再是春天
——夏
在满山横斜的枝条上
结满
绿色的“果实”
青涩只等人来
——变身,且成就
一场心灵与身体的坚硬
复静中亦再软化为路
只,错皆不拥花香
惊,而不关天门
见与不见
——都是巍峨与沟壑
川藏线
——如果你此生没有意识到尘世的辽阔那么不防放下世事的纠缠
去一趟西藏
在你亲身经历过极度的
缺氧
在和死神擦肩之前
你会看到
美丽的格桑花儿开在辽阔之上
你也会看见
此生的来处,也曾烈烈飘动的经幡(引子)
车过巴塘
——我闻见在身子上面
飘荡着
刺鼻的橡胶味
我想
该是要死了,车轮一再碾过我的虚弱
人啊!
只有在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之后
才明白
死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
在沙漠
我曾经从嘴里吐过沙子
哪里除了太阳毒辣
就是嘴唇渗血
现在
我才知道
身处在的高原,氧气
是多么稀薄
然乌湖的湖水
——躺着
神女——圣洁
不好拿出来的污秽,还是
随我
将死亦或是将生吧
如果你能理解古老的冰川
那就能理解
我在冰川之下的生还
——拉萨布达拉宫高高的白墙
墙内,身着红袍的
僧
山城
雨——总是在你不经意时落下
习惯了它的人
随时都在准备着携伞穿行
我是一个外来客
是
心怀着一个异乡来接纳一座新城的
城待我
——却一如宽阔的江面之上三三两两之轮渡
因为习惯,而总要成为血亲
我是总觉得
白昼应当是一个长修的行者
而夜
满城的灯火如佛
那落在旧日门楣上的手,推开的
在北方的冬天,一只手穿过白昼的灰烬攀上了门环它正欲作势叩响,这长满铁锈的门——
门满身锈渍,站在那里
在吞下无数个日月后,隐隐约约长出了满口獠牙
我现在是一只被时间遗弃了的跛脚怪啊
在一片混沌的慌乱中——
试图踏过,这腐朽
风在一次次吹动,冻土里这无比僵硬的北方
可惜我不是一只飞雀,无法借了它势
越过眼前这一片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