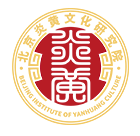黑伙头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睁开眼,他爹就这样说他,到五六岁时他耳朵就快磨出茧子来,黑伙头第一次学会给他爹顶嘴说:“我就要娶老婆,娶八个,娶一百个!”这种现象也许是因他爹总是贬低他,才造成了幼小心灵有了第一次反抗。
也许是从小受到爹爹的贬低,伙头从小就有偏迷异性倾向,只要有女孩从他面前走过,他两只眼睛就会死死的盯着,直到人消失了,他的目光还呆滞的望着。村里的老娘们见到他这种异常行为,说:“黑伙头这孩子长大一准是个水逛货(流氓)。”
黑伙头到了上学的年龄,也没有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论学习,论智力,论说话再正常不过了。他的性格骤然变化还是刚从上初中起,自打一进初中学校他两眼就盯上了班里的一个叫二花的女生,两眼好象一辈子不打算离开一样,盯得二花心里发慌,二花就报告了老师,调皮男生就起了哄:“黑伙头二花啷得个啷!”俏皮的女生咬耳朵:“二花要嫁黑伙头有肉吃,黑伙头两片嘴唇能调两盘莱呢。黑伙头的眼皮肿囊囊是看二花累的,哈哈哈!”其实她们声音虽小,黑伙头也是听得到的,因为黑伙头的座位就在她们后排。同学们有事没事就拿黑伙头开玩笑,女生们也斜着眼瞟他,捂着嘴笑他。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老师找他谈话,批评他不该看女生,行为不正当,属于下流。黑伙头顶撞老师:“那你每天都看女生是啥行为?”把老师气得找家长告状,他爹把他一顿苦打,话往狠里骂:“娘的,长得没人型,驴头驴脸的净干流氓事,丢人败德的东西,别上学了,拿书包滚回来!”
黒伙头十三岁辍学务农,没有男伙伴一起玩,更没有女孩敢接近他。他心情好陏闷,他心里说不就是黑点丑点吗,他审视自己站在镜子面前,张嘴看看嘴里子就是黑的,两片又厚又大的嘴唇总也合不住,一张口满嘴黄牙,一双肿眼泡就象两个核桃瓢一样,衬托着一双小眼睛异常发亮,他越看自已越觉得自已长得寒颤。他骂自己,心里还敢装进二花,真是不要脸,看看人家二花啥长相,自己啥长相?真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越想他越觉着自己丢人。照着自己狠抽两个大嘴巴。他爹进来见他他抽自已嘴巴,问”干啥呢?干啥呢?"黑伙头听到他爹猛不丁在身后吼,转身正和老爹打了个照面,心中紧张,有些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想二花……”他爹一听来了气:“想二花,想二花,没出息的东西,老婆子迷。”他爹气哼哼的走出屋去。其实黑伙头想说,他看二花并非是下作,只是看看罢了。这句话他爹没听下去,他只能对墙说了。黑伙头又想起二花,不就是我长得黑吗,不就是多看你一眼吗,干嘛非报告给老师不可。为什么王支书的儿子拉着你、拧你,按住你胳肢,你还贱笑。老子是长得黑点丑点,等老子将来有了钱还不要你呢!黑伙头有些愤愤不平。
黒伙头长到十八九岁,身体健壮挺拔,只是长相依然的又黑又丑。他的性格极端的改变。他不再看任何女人,话越来越少,羞于见人。每天收工后一头钻进自已的住室内,室內黑古隆咚的,窗户很小,父亲偏偏又在上面安了个鸡窝,把光线遮挡起来,这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从此黒伙头上工干活慢慢腾腾,工间歇息的时候躲人群躲得远远的,坐在地上两腿拱着,头伏在两个膝盖上,俨如一条休眠的蛇。一边平辈的嫂子们见到他这个样子就挑逗他,冲他喊:“伙头过来!”黑伙头懒洋洋的抬起头来,见翠嫂向他招手。翠嫂笑得如一缕春风,他就走过去蹲在翠嫂身边。翠嫂一边纳着鞋底一边问:“伙头!今年多大啦?”翠嫂的声音就象泉水叮咚。伙头答“十九!”翠嫂拿眼盯着他说:“噢!该成家了,给你说个媳妇吧?”黑伙头“嗯”一声,翠嫂显得十分亲昵的说:“回家给咱达说一声,炸两篮油果子,再称几斤鸡蛋,”翠嫂仔细看着黑伙头,继续说:“她啊,长得大高婆娘,俩大眼,黑展展的,一条大辫子,中不?”翠嫂又拿眼瞅他。“中”,黑伙头满脸羞涩不敢和翠嫂对视。翠嫂又说:“咱可说好,你可别嫌弃人家,我觉着你两很般配。“嗯”黑伙头有些激动。翠嫂便把声音提到高八度说:“她就是长了四条腿!”直到这时伙头这才明白翠嫂是拿他开涮,编着空儿骂他。黑伙头顿时满面羞愧起身躲得远远的。引得一群做针线的女人哄堂大笑。她们却不知这句玩笑深深刺痛了伙头的心,伙头拿眼望一下不远处的一头大黑驴,栓在树桩上,浑身黑呼呼的,糙糙毛毛,垂头搭拉脑的,两只眼角布满眼屎,下唇一边歪着,显得真是肮脏。他想或许翠嫂嘲笑他象那头驴。伙头象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泪滴直在眼框里转,翠嫂见状就从面前的竹篮里拿出一根黄瓜塞给黑伙头,她随即哄道,“弟啊!嫂子逗你玩呢,赶明儿只要有合适的媒茬,嫂子一定帮你说”伙头眼泪瞬间流了出来,翠嫂哈哈笑着骂道:“你个叉拉着(骂女人)看你小性的”。她随手一挥抹去了伙头的两行泪水。伙头并非是翠嫂想得那样,他是太激动了,队里干活休息时给女劳力分黄瓜,男劳力是没有的,伙头没了娘,他跟着妇女干活,只有翠嫂常常把自已的一份分一些给他,伙头是感动得流泪,只是不善言表罢了。
随着年龄增长伙头更加自卑。
生产队那会儿,别管吃好吃赖,或穷或富,社员们干起活来情绪十分高涨。那年三伏天,队里搞高温积肥,土堆堆得象小山一样,垫起了一个长长的跑道,用力车还往土堆顶上盘土盘草皮,三个男劳力编一班,实行包工。人啊拉着重车哇哇叫着往土堆顶上冲。黑伙头与人搭班,腿象灌铅一样,步子跑不快迈不开,让人更可气的是,冲到半坡上正是需要齐心合力的时候,伙头猛然丟掉拉绳,蹲下去脱鞋子,这下可好,车子倒了下去,掌把人拽不住,车子脱手而去,力车负着重带着惯性,箭头一样朝下冲去,把正在下面平路的队长一下撞出一丈开外,当场昏死过去。那年月队长就是土皇帝,迎逢巴结的人居多,队里保管员八赖子,会汁老纠看到了黑伙头的行为,当场围住黑伙头拳打脚踢,伙头被打得在地上“哇哇”惨叫,分辩道;“我脚被扎了,我脚被扎了”,翠嫂一旁冲了过来,左推右拦的来护黑伙头并好言劝阻八赖子和老纠:“伙头是个没娘的孩子,老话说抬手不打无娘子,开口不骂年老人”八赖子老纠哪里听劝,只管往狠处打,愈打愈凶,黑伙头不知哪来的劲,从地上一下拱了起来,抱住老纠的右手,咔嚓一声,三根指头被咬了下来,只听老纠一声尖叫,在地上一阵翻滚,伙头象出了恶气,噗地一口把三个断指吐了出来,竞然恶作剧的笑了起来,笑得八赖子毛骨悚然,八赖子顺手操起一把铁锨,翠嫂猛地扑向黑伙头大声招呼伙头,并奋力推开黑伙头,“伙头快跑!”翠嫂阻拦下八赖子。
伙头这一跑就是四十年,村里人早已把他忘记,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村头百年的的老槐下,停下了一辆豪车,顿时引来了半个村子的人,有人认识这是一辆林肯,众村民一阵咋舌议论,一个粗壮挺拔,穿着光鲜的男士笑迎众人,身后跟着一位衣着华贵的妇人,村里的一位老人认出了面前的这个男人,老人惊叫:“这是伙头吗?”
“是我!”伙头一把拉过老人的手紧紧握住,亲切叫道:“长顺哥”伙头还认识,长顺是翠嫂的男人,伙头迫不及待的问,“哥!我翠嫂呢?”这时候人群里钻出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年妇女,“伙头,你个叉拉着这些年都到哪去了?!光听着你跟着人家出国了。”
伙头顿时热泪盈眶,一声“嫂子!”叫着,孩子般的向翠嫂迎了过去!
剪辑碎片故事:
远近十里八村,都知道长顺有一个富豪弟弟,长顺的三个儿子都娶上了漂亮的媳妇,只因正当大儿子二十岁那年,长顺收到了一笔海外汇款,一笔60万,这是一件爆炸性新闻。长顺和翠嫂猜测是当年翠嫂娘送人的丑弟弟。
长顺两口子千回百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弟弟却是穷得叮当响的最穷的山里人。
改革开放的第五个年头,长顺所在的镇政府收到了500万捐款,是资助建学校用的。省台记者通过多方调查,这笔捐款是一个华侨,当年怀揣着嫂子塞给的一头膘猪钱落荒而逃的人,逃难中他遇上一艘渔轮,船长看上了的他健壮的体格,有幸被征用,后在洛杉矶做生意。
翠嫂又猜是伙头寄回来的,此话传到八赖子耳朵里,八赖子断言,“发财的机会象雨点一样,也难落他头上一滴。”
长顺大儿子给弟弟们讲,当年伙头叔出逃时,娘把一头膘猪线塞给了伙头叔,娘说,她只要一看见伙头叔,就想起了姥姥送人的丑舅舅。